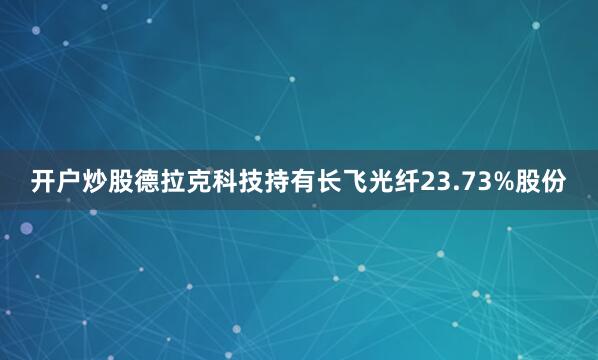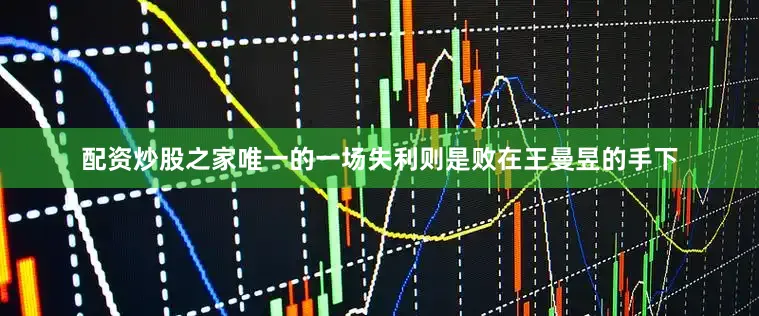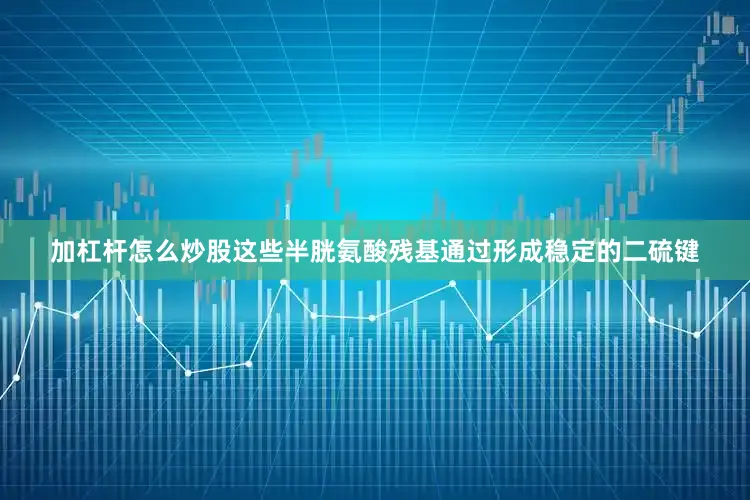(来源:中国政府采购报)
转自:中国政府采购报
【舌尖上的文化】
豆豉里的黄土情
■ 司润和
榆林往北,黄土丘陵一路伏延又突起,便到了麻黄梁镇。本地人熟络地讲:“咱这搭,有一样吃食最离不开。”那便是麻黄梁的酱豆腐和豆豉。
这片梁上的老镇子,巷道如老人曲折的筋脉般兜转,风过时,仿佛能捎来豆子的微醺暖香、蒸腾的水汽与花椒的鲜麻气息。此地人皆守着古法做着酱豆腐与豆豉,各家微小的作坊便如镇子的心跳,安稳地搏动在每一道门槛后面。镇东头的李玉梅家,便是如此一方灶火。“乡党都来我家寻。”刚过六十的李大妈总是带着厚道的笑意,“打年轻时候就围着这锅台转弄酱豆腐,手脚没闲过哩。”
说罢,她便引我们走进自家院子,黄土坡上几孔老窑洞安然落座。李大妈径直推开偏房一扇旧木门,这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屋子就是她的小天地。墙角陶缸静静码放着,封存的是自家酿的糜子黄酒,这酱豆腐和豆豉是点睛之笔。屋子当中地上,排列着数只黑色老陶坛,里头就是正悄悄酝酿滋味的酱豆腐坯子和豆豉胚。李大妈说,此地人家家都有熬做酱豆腐的习惯。“我娃娃还小那会儿,老人见哈气成霜的窑洞当口就讲,酱豆腐要备哩!年景少了这一口咥着,咋能叫过年嘛!”
展开剩余62%到了真正阖家团圆的年三十夜,热菜的香气在窑洞里蒸腾缭绕,最后端上炕桌的,必是那切得方方正正、遍身胭脂红的酱豆腐,旁边少不了油润润的一碟豆豉。
豆豉的做法看着质朴简单。拣当年的新豆子,隔夜泡发透了,次日用大铁锅滚水煮熟,沥干水分,随后便赶紧用干净的白粗布密实包裹起来,整盘塞进柳条筐,再紧紧捂上麦秸与旧棉絮,放到阴凉背静处等着自然生发奇妙的转化,这过程约莫得等上半月光景。
待到时辰足了,李大妈才小心掀开包裹布,此时那发酵好的淡色豆豉已经暗藏神韵了。她将豆豉倾入盆中,再兑入珍藏的原汤精华,添上盐、醇厚的黄酒、姜末,最后加入花椒粉与喷香的辣面子搅匀,封存在坛里腌渍些日子便得了风味。看似平常,却暗含老辈人才懂的节点。盐放少了吧,豆豉面儿便虚浮起一层白霜,味道也走了酸;可若是错过了豆豉刚起酵、粒子正饥渴吸收滋味的那寸光阴再加盐,咸味就吃不透里头去了。李大妈边利落地拌着调料边轻声念道:“盐跟时辰,都在自家心里装着哩,旁人摸不清这个路数。”
而做酱豆腐,豆子倒是不必太挑。细心磨成豆浆点成豆腐,压出水分切成寸许方块。接着便是最需耐心的一步:柳筐底下铺匀晒得干脆的陈年麦草秆,豆腐块像砌小城一样整齐地码放上去,盖一层草秆,再码放一层豆腐块,如同反复而安稳地累积堆叠。待装筐完毕,将盖子封严实后搬到阴凉的窑里养着,李大妈这时会特意撒一把陈年的艾草屑在麦草秆上。她笑眯眯地说:“艾草那个清气,是老辈人传下的念想,打小闻惯了这个,坛子里捂出的味才正。”
有年轻后生曾好奇地问过,如今机器利索得很,何必这般慢腾腾费手劲?李大妈只是含笑摇摇头,这祖辈相传的工夫确实缓慢,然而慢处生出的味,是豆子与手温与黄土在岁月里从容对话,才沉淀下的浑厚心音。若失了这种慢,舌尖上那份独特的、安定的浓香便仿佛被抽去了魂灵。
那些黑褐的陶坛静立幽暗处,豆子在时间深处秘造自身。待个把月后开坛,酱豆腐与豆豉终于被慎重取出,它们早已将麻黄梁的风日雨露、温热厚道、黄土深处无声而坚韧的生息,悄悄酿进细密肌理里。它们自身便是小小的一方陕北乡土,方方正正,滋味笃厚,是时间以最缓慢的方式写给土地的味觉箴言。
本报拥有此文版权,若需转载或复制,请注明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报,标注作者,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。否则,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发布于:北京市灵菲配资-在线配资公司-好股配资网-杠杆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