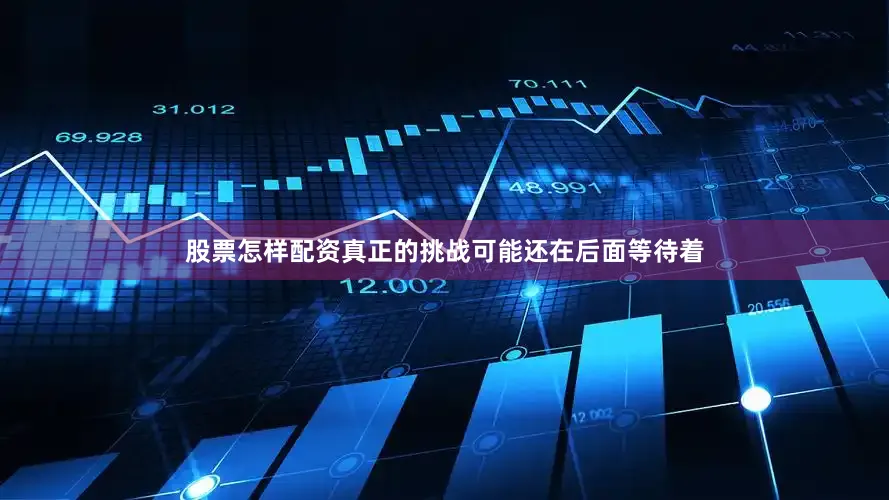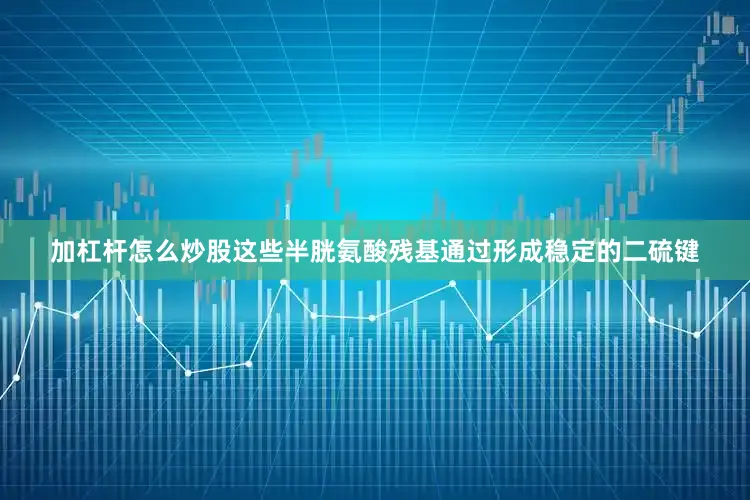改写后的文章:
写作并非易事,每位作者每天都在辛勤耕耘,只为能够养家糊口。希望亲爱的读者们多一份理解与支持。为了更好地阅读内容,文中加入了5秒钟广告解锁,观看5秒广告后,就能免费观看文章的全部内容。感谢各位的支持与配合~~~
文| 王淮正
编辑| T
1970年代的一个清晨,在河北某个生产队的田地旁,随着第一声鸡鸣破晓,社员们扛着沉重的锄头,脸上带着一丝倦意,慢慢地步入田间。突然,一声尖锐的哨响打破了宁静,社员们纷纷分散开来,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劳动。
展开剩余86%当队长老刘看到稀疏的劳动场面时,不禁皱起了眉头:“这些人,真是没什么干劲啊!”他心里明白,靠那点工分,谁又能拼命干活呢?到底是社员们太懒了,还是制度让他们只能“走个形式”?
在生产队的那个年代,工分制几乎家喻户晓。说到工分制,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激励社员劳动的一大动力。毕竟,每干一天活就能获得工分,年底还能用工分换粮、换钱。但如果深入探讨,工分制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看得上,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
一旦工分制实行,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套体系中的位置——有的干活儿的老把式,做事认真;有的却只是磨洋工,做个“懒把式”,这种差距很容易看出来。
然而,工分制最初的设计是按人头算的,这意味着“干得多”和“干得少”的工分差距并不大。结果,干活积极的老李头、王大婶开始抱怨:“再怎么卖力地干,工分也不比那些混日子的少,这哪算得上激励?”于是,生产队里的情绪两极化了:一边是想着怎么少干活却不落后,另一边是默默辛勤,却始终积累不到足够的工分。
那些勤劳的社员本来想着多做几分活,争取多赚点工分,可渐渐地,他们发现辛辛苦苦挣得工分,最后换来的却只是寡淡的生活,甚至有人开玩笑说:“一天到晚胳膊酸、腿儿疼,拿着工分回家做‘寡汤’,真是人也难,汤也寡。”
在这种机制下,社员们的劳动热情就像是被扎破的气球。那些想拼劲儿干活的人,也逐渐发现:即使努力了,得到的回报也有限,最后很多人都开始“混水摸鱼”,得过且过。
然而,并非所有的生产队都这么松散。有些管理较为严格的队伍,队长和生产小组长都会密切盯着社员们的表现。一旦发现有人磨洋工,立即就会被督促加把劲。
这些生产队里,社员们几乎可以感受到队长锐利的眼神,比苍蝇还要毒。想偷懒几乎没有机会。
但是,也有一些心思灵活的社员,发现了工分制的“门道”:反正无论干多少,挣得差不多,干嘛要自己累得像头牛一样呢?于是,他们干脆扛起锄头,慢悠悠地在田间转悠。结果,许多生产队里出现了“表面劳动,实际偷懒”的现象。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“出工不出力”,大家依然来到田地里,假装干活,但锄头下的力气显然大打折扣。
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步实施,这种“走个形式”的现象也开始暴露,大家对于工分的热情显然下降了。社员们开始意识到,工分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报,劳动的动力越来越小。
在这些生产队里,队长与社员之间,犹如猫和老鼠,双方不断斗智斗勇。每天清晨,社员们面带倦容,拖着锄头走向田间,虽然心里早已明白“形式化”是常态,但外表依然要装出一副在努力干活的模样。
但是,有些生产队对偷懒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。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,有的队伍甚至实行了“轮岗制”,每天指定监督员来监督其他人,谁磨洋工,谁就立刻被点名批评。
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。毕竟,社员们在田间工作时间久了,互相之间难免建立起了一定的人情关系。很多监督员对邻居们不忍心指责,于是有时对偷懒现象视而不见。
某些小队甚至自嘲地将“轮岗制”当作形式,大家心照不宣:“今天你监督我,明天我监督你,大家互相体谅,偷懒的大伙儿心照不宣。”
这种复杂的人情和制度矛盾,最终导致社员们的劳动效率低下,尤其是在那些管理松散的生产队,偷懒现象成了家常便饭。许多社员们变成了“集体小偷”,各自都有些“独门绝技”:
有的社员通过“早起晚归”来混淆出勤,假装自己出工多;有的则躲在队长的视线盲区里,消磨时间。而队长们对此感到头疼,但往往也懒得去管。于是,这种“偷懒与反偷懒”的拉锯战,几乎成了每一天的日常。
在那段时间,社员们的干劲儿与偷懒并没有明确的界限。这一切其实取决于当时的激励机制、管理模式,以及社员的内心状态。直到1978年,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犹如一剂强心针,直接刺激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。
包产到户之后,田地被分配到各家各户,社员们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,而剩余的粮食也可以自由支配。这种变化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付出与收获之间的直接联系,大家纷纷振作起来,全力以赴投入劳动。
小岗村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。那些曾经偷懒的社员们,看到干得多、得得多的回报后,纷纷拿起锄头,劲头十足。生产责任制取代了原来的工分制,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幅提高,社会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回想起当时生产队的情景,许多社员对工分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:“别说一锄头能挣几毛钱了,这一锄头下去,估计我自己都能累个半死。”
在没有明确利益激励的情况下,劳动变成了“例行公事”,大家的干劲自然也不高。而小岗村的成功却证明了:适当的激励与自主权,才是激发干劲的真正来源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生产队时期社员们看似在“混日子”,但并不是没有人愿意干活,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合适的制度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。
参考资料:
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——以20世纪70年代河北某生产队为例 中国农村研究网 2016-10-19
发布于:天津市灵菲配资-在线配资公司-好股配资网-杠杆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